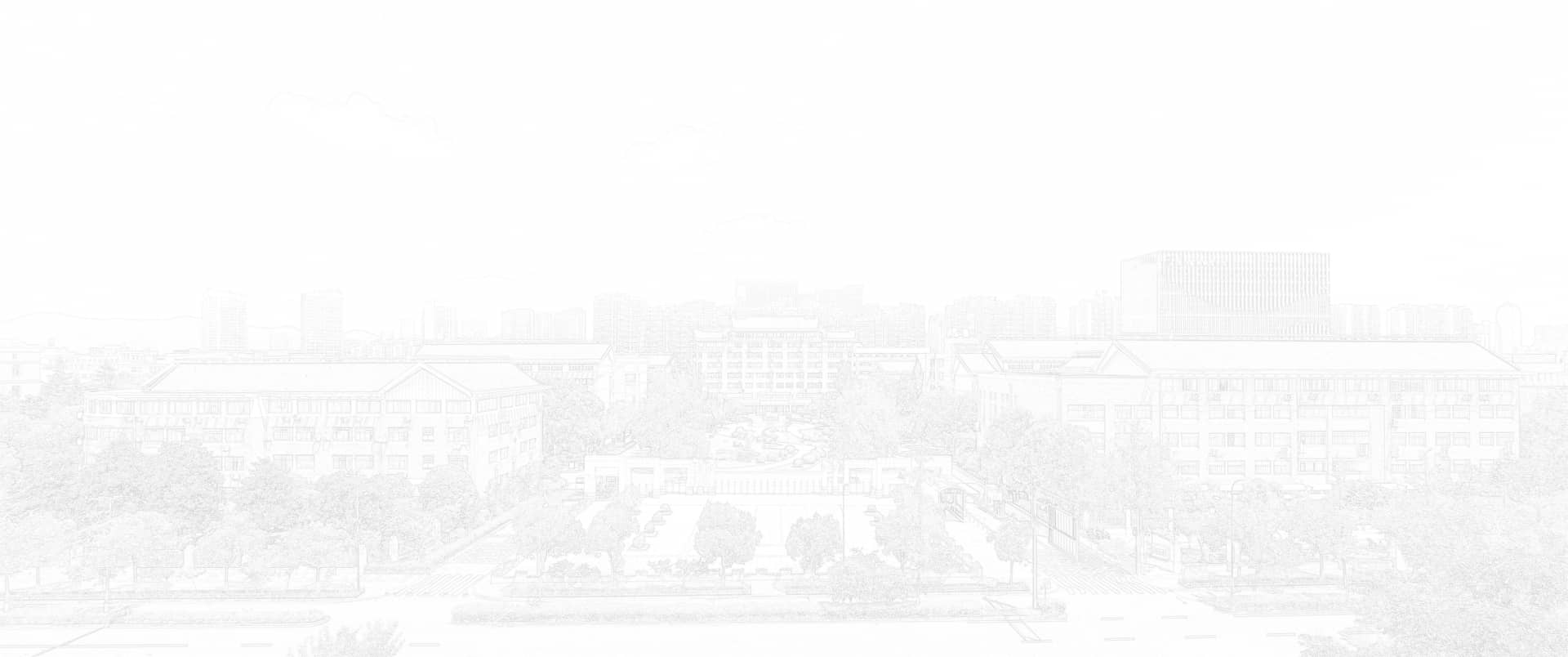陈醉首先对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的士”、“菲林”等用语进行分析,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殖民文化造成的。但现在很多中文报纸也大量夹用英文原词,这种现象说明了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不仅日常生活中如此,现在艺术界包括美术界也有类似情况。
面对全球化环境,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陈醉指出,我们一定要提倡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没有民族自尊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他说,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为争取自尊有三次大事。第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族”问题——三民主义,在艺术方面有个细节也可以体现:“中山装”的设计。第二次是“五四”运动,其表面形式看似反传统,但究其实质是为了复兴中华,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第三次是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民族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陈醉表示,现在“全球化”这个词在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用得很多,但文化、艺术能否“全球化”就很值得商榷。他用绘画中的具体例子说明文化在理论上并不存在先进或者落后的问题,西方的油画和中国画各有所长。表达重要历史事件时,油画要更胜一筹,但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和西洋画中的“小爱神丘比特”从靠近艺术本质的角度看显然“飞天”更能体现人类想象的造诣。
陈醉在讲座中进一步指出,文化环境的变化已经不是纯学术的问题,而要放到文化战略的高度,重新振兴我们的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尊。中国的文化市场现在还留有很多空白。国外的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不断向我国推销大片、动漫,甚至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他们的“孙悟空”、“孔雀东南飞”。他们从吃穿用到文化欣赏不断改变着我们的民族趣味,消磨我们的民族精神。陈醉还指出,“民族劣根性”的提法是很不科学的,因为中华民族的“根”是优秀的:经济上,汉唐时期甚至原始时代不“劣”;从文化形态来说,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更是辉煌灿烂。我们的创作学习和艺术实践一方面要很好地继承民族传统,同时也要很认真地学习异域的先进文化补充自己。我们要提倡民族精神,但不搞“民族主义”;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不搞全盘西化;不盲目崇洋,但也决不“夜郎自大”。
面对来自艺术学院的学生听众,陈醉先生鼓励他们注重人文科学的学习,因为除去技巧的基本功训练,艺术的真正较量是看文化素养。要成为一名艺术家,天赋、机遇、勤奋缺一不可,同时心态也要好:创作时要把心底的悸动表达出来,这样其他人看该作品时才会产生悸动、共鸣。